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大学以德国大学为样板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需求为基本动力,以多元化为主要特征,最终成就了美国大学的崛起和美国世纪的产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译丛·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就是解读上述背景下美国大学在20世纪“何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经典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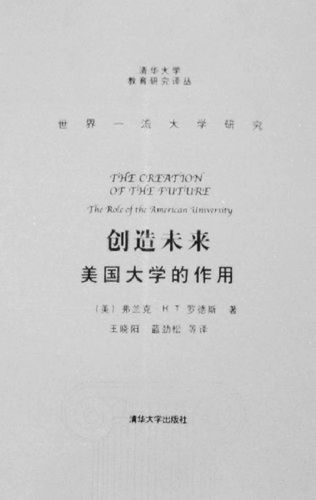
1889年,美国的一个银行家宣布,不再聘用一个大学毕业生。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同时嘲笑大学生们在那里学习已经死去的语言,好象是在适应另一个星球上的生活。同年,50万来自德国、英国、爱尔兰、意大利和波兰的劳工移入美国,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新力量。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就后一事件评论说,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孩子急于抛弃自己旧的国民性,准备成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不过这有赖于“美国环境的教育和同化力量”。
银行家和钢铁大王的态度,显示出企业界对大学教育的敌意和藐视。而欧洲移民对“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的追寻,表明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这两种相互抵触的力量,构成了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加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大学的危机感,加速了大学的迅速转型。在此前后,美国大学以德国大学为样板进行改革,这一改革以适应社会需求为基本动力,以多元化为主要特征,最后推动了美国这一列“飞驰的列车隆隆前进”,成就了美国世纪的产生和美国大学的崛起。包括《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令人骄傲的传统与充满挑战的未来:威斯康星大学150年》等5本书在内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译丛·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就是解读上述背景下美国大学“何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经典之作。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研究型大学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行业的发展而快速崛起。“研究型大学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这是弗兰克·H.T.罗德斯在《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中的基本观点。作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荣誉退休校长,罗德斯立足于自己丰富的个人经历,在书中深入讨论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发展、现状、未来、地位及作用。他用学术自由与卓越的校长领导,得到私人支持和承担社会责任,植根于本国而具有国际视野,学术独立的同时担当建设性的合作伙伴,以学生为中心、以知识为基础、以教育为中心、以研究为推动力,由高科技武装同时对社区仍有依赖性,追求高质量和高效率,专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结合等8个特点来描述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作者认为,大学存在的基本理由就是从共享的对话中获利,学术共同体是大学的本质特征。但随着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学术共同体正在走向衰落——以专业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文社会科学在大学中的影响力减弱,学科间的对话、质疑、讨论和争辩逐渐减少,学术共同体日趋式微。总体而言,作者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未来发展态度乐观自信。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历程对中国一流大学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公立大学是美国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于1848年的威斯康星大学,是全美最顶尖的公立大学之一。它把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联在一起,突破了以往大学教学科研的二元职能模式,把大学从社会的边缘推向社会的中心,由此威斯康星大学成为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典范和旗舰。该书是为纪念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成立150年而编辑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作者认为,威斯康星大学要评估自己的优势、摸清潜在的服务对象、开拓自己的发展空间,从而找到自己合理的战略位置,而不是一味地效仿研究型大学。面向未来,威斯康星大学将实施创新性策略,并保持策略的敏捷性和灵活性,“不再把教学、研究和服务当做相互分离的活动来努力加以平衡”,而是围绕“学习”这一主题,从学习经历、学习社区和学习环境3个方面,承担大学的职能并推动战略目标的实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威斯康星大学确立了保持科研领先地位、重构本科教学、融入全球化社区、更新大学理念4项优先工程。此外,作为一所公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将不单纯依赖州政府拨款,而是将“积极利用捐款资源和教师争取到的校外资助经费”来保持其强劲的竞争力和优越地位。公立大学是中国大学的主体,无疑,威斯康星大学在20世纪的杰出表现及其未来战略,对中国大学不无启发。
现代大学早已走出象牙之塔,与国际政治局势、国家意识形态、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崇尚“学术自由”、志在“服务社会”的美国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对政府经费和与之相伴的国家权力有着一种本能的抵触。那么这些大学是如何适应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需求的?《创建冷战大学:斯坦福大学的转型》用社会史学的研究方法和个体行为发生机制的研究范式,考察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期间,在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下,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美国顶尖私立大学如何从国家政治经济的边缘逐步走向中心,并由此引发大学内部制度、科研经费体系、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作者认为,支撑冷战期间斯坦福大学骤然崛起的制度基础是大学制度由学术自由主义向学术资本主义的转变,与前者对应的是多元巨型大学,与后者对应的则是冷战大学。完成这一转变的两项制度安排是“合同制度”和“间接费用制度”,这两项制度确保在政府资金注入大学的同时,大学学术自由和办学自主权不受侵犯。通过这本书,我们会看到国际政治、国家权力、政府政策对大学制度、大学职能、大学治理的影响,也会看到美国大学对学术自由、自主治理的格外珍视。
该丛书中的另外两本是《哈佛走向现代:美国大学的崛起》和《麻省理工学院和创业科学的兴起》。前者是论述哈佛大学在20世纪后三分之二的时间里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力作,透过700余页的文字,我们会看到哈佛何以卓越、何以伟大。20世纪以来,大学的职能从教学和科研扩展到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等领域,大学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大学职能的扩展,推动了创业型大学的崛起。《麻省理工学院和创业科学的兴起》则是一本分析大学在社会中的职能转变和创业型大学崛起的权威著作。
今天,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涌向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跨国企业对美国一流大学的高材生们也敞开着大门,一个世纪前银行家和钢铁大王的态度对美国大学来说已成为永远的过去。在美国大学成功转型100年后,中国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全面推动高校扩招、推进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阶段迈进的同时,明确提出在中国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笔者相信,“清华大学教育研究译丛·世界一流大学研究”首批的5本书,对中国大学在新世纪的成功转型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贾宝余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7-12-13)
读了四年大学,又开始读研究生,在校园里浸泡这么长时间,现在反思一下大学生活,突然觉得,大学生活尽管很自由,但是有一种病态的自由正在改写着自由的真正的含义。“自由”就是指个人可以主动地选择,但是很多学生都不知道怎么把握自己的自由。大学里流行两个词语,一个是“无聊”,一个是“郁闷”。“无聊”是指一种无所事事、茫然的心理状态,当“无聊病”发作时,很多人就迷恋上网游、聊天、流行读物等等各种消磨时间的方法;而“郁闷”大抵是指各种各样的资格考试、等级考试以及频繁的面试、应聘等事,如果没有利益的牵引,他们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这些活动。所以“郁闷病”是“无聊病”的反面,前者是忙时的不自由,后者是闲时的不自由。
忙时的不自由根源在于教育体制的弊病,中国的大学大抵还延续着应试教育和填鸭教育的模式,低效而苦力的劳动,确实不容易让人感到学习的快乐。这种反思是很多的,也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校园生活“闲时”的不自由却往往被人忽略。对之进行分析,或许可以解释当前大学生的普遍精神状态,回答大学生群体存在的共同问题。在笔者看来,对闲暇时间毫无意义的消磨,源自校园“公共空间”的萎缩,正如西方社会遭遇的公共领域沦丧,让人们丧失激情、忍受孤独一样,中国的大学也正遭受着公共领域沦丧带来的困扰。
一方面,个人化的电子技术的普及,成功地挤压了校园“公共空间”。身边很多学生,除了上课,几乎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在网络中度过,校园生存呈现一种“原子化”的分散状态。MP3堵上了交流的耳朵,个人电脑和娱乐手机遮蔽了欣赏他人的眼睛,因此自由的闲暇时间不能被快乐的使用,而成了“killtime”(杀死时间)。学生们的寂寞情怀、孤独心理无法得到正常宣泄,因此生出网络愤青、网游综合征,以及更为普遍的无聊心理。
另一方面,随着扩招和“校漂族”的增多,学校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却远远跟不上。有的学生上了4年学,都没有参加过几次正规的学生活动,甚至都不知道学校还有一个可容纳几百人的小剧院!更多的学生活动变成了官方主持一个仪式,大部分是强迫参加的,当然也是趣味索然。而学生自己组织的活动,往往因为得不到校园服务部门的支持,甚至有的学校因操场人多混乱便加锁管理,不让使用。有的学生工作人员(包括一些学生会)官僚气息严重,根本不理解学生,缺乏起码的服务意识。校园应该提供给年轻学子们一个公共空间,用来交流知识、交流情感、构想社会、指点江山、展示青春的活力和浪漫,可悲的是,因为落后的公共设施和管理理念,这样的空间却基本萎缩殆尽。
学校变成了一个机构,到处都是少数人可以监管多数人的空间(如教室、宿舍、食堂),而那种多数人围绕少数对象进行交流的公共空间,却正在消失。大学再也没有那种广场一般活跃和辉煌的气度了。诗人于坚在《尚义街六号》中描写的大学诗友们聚集在一起,探讨诗艺、交流心得、探讨创作的“沙龙”,对当代的学生来说,太陌生了!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相比,这一代学生物质上无疑是丰裕的,但他们在精神上却是痛苦、迷茫的。笔者以为,缺乏一个可供年轻人展示自己、实现自己、与人交流的公共空间,对大学生精神的戕害相当严重。大学看似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身处其中的人,年轻的学生们,却被孤独地禁闭在窄小的自我空间里,不能自拔,渐渐窒息。
(作者:孟随 来源:中青报 发布时间:2007-11-20)